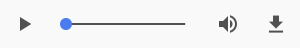
2022年3月,疫情还在肆虐,刺桐花开,一夜风雨,满地飘零。原本多情安逸的历史文化名城也被迫按下了暂停键。都说泉州是一座让时间静止的城市,可当她真正静止了,人们都在忐忑不安地生活着,又有多少人去顾念着一个即将离开的“老学徒”?三百公里的距离,成了他退休前的一个遗憾,以至于退休手续都是让隔离在单位的同事代办的。
“老学徒”是他为自己四十三年逾四个月工作履历贴上的一块谦卑的标签。如此称号至今都没人传开,因为不知多少学徒承袭了他的“衣钵”,为友为徒,自然不敢僭越。于是,只有他这样自谦地介绍着。
常驻大田的人
2011年初春,春寒料峭,当空气中还弥漫着春节喜庆味时,我已只身前去大田。为了方便对接业务,单位在大田设置有一个办事处。兰工,便是常驻办事处的人。当时迎接我的是他和他爱人,一对年近半百的慈祥“老人”。初见并没有过多热情,这倒让我轻松许多,都是慢热、淳朴的地质人,这种待人方式更让人亲近。接触后才知道我们老家在同一个地方,因语言上的顺畅和生活方式的相同,熟络起来也就更快了。为了弥补之前因照顾孩子不能长期在一起的遗憾(也是大部分地质人的遗憾),也为了方便照顾他生活起居,他爱人便常年跟着他东奔西走。
寒暑易节,人来人往,只有他常驻大田。后来才知道单位要依托大田这么一个窗口,让他培养年轻人。尤其是2011年后,随着单位对外窗口的扩大、综合业务能力的提升,业务量呈爆炸式增长,人才的引进力度加大。大田作为单位培养年轻人的基地,除了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更重要的是有一个“老学徒”可以尽情地依托项目培养新生力量。每年补充的年轻血液都会下沉到大田办事处,他的徒弟也慢慢多起来了,尊敬称他一声“师傅”的越来越多。而他总会谦虚地说:“你们一个个都是大学生,我一个高中生,充其量就是一个老学徒,哪里当得了你们的师傅。”后来有人再很正式地称呼他“师傅”时,他都会以“老学徒”自居,从此“老学徒”这个标签一直未曾撕下,只是没人敢这么称呼罢了。
在以后近1000个日子里,我跟着“老学徒”一起走遍了大田18个乡镇,尝尽了大田各种小吃。高才坂、雄峰、银石坪、元山、大坑、下地、上峰、东坑……从大田的最南端到最北端,用双脚共同丈量着大田地区的矿产厚度;石灰岩矿、高岭土矿、铅锌矿、铜矿、煤矿……从非金属矿产到金属矿产、能源矿产勘查,用双手一起勾绘出闽中成矿带的矿产丰度。年龄的跨度,并没有阻断我和他相互学习的距离,彼此互为师徒,在不同的勘查领域取长补短、相互借鉴。他以各矿区为实例,总结不同层段岩性的识别、矿化蚀变的判别标志;而我在室内资料综合整理、研究方面给予充分完善补充,野外、室内互补配合,共同完成了一个又一个项目。
十年再见
少小离家,回首已花甲。十年的长度于宇宙的广度与深度来讲,是微乎其微的,但于人的一生却是厚重而漫长。十年前,初识“老学徒”,从未想过会有分别。相识十年后,离别悄然而至,且来得如此仓促,以至于除了接受短暂相聚的甜与即将分别的苦,别无选择。
刺桐花开不知多少个四月,东西塔依然巍峨肃穆,或许都是在等待着他的归来。然而因为疫情,待他再次回泉,他已不再是“一九七”人,只能算是前员工、前同事。于是忙着预约请客吃饭,一叙旧情以挽留最后的一丝共情,酒过三盏,除了祝福退休快乐,再无他话。对于其他人来说这一别也许就是再也不见了,而于我则是再没人可以聊着客家话讨论矿产勘查的前景与“一九七”的繁荣壮大……
记忆中“老学徒”一直都是开朗、勤快的存在,虽然近退休了,仍坚持在野外一线,坚守着地质人的初心,从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很多人不理解都块退休了,何以仍然坚持在野外?但他总能风轻云淡地说,他习惯了野外这种无拘无束的自由,更习惯野外这种零距离亲近地质现场的心安。前几年,家道突遭变故,知道的人都觉得他这次估计要消沉了,但出乎大家意料,工作中,他依然“我行我素”,全然没有受家里变故的一丝影响,公事、私事截然分明。有人不解,难道没有你,这单位真没法运转了?他说,“每天怨声哀道又不能解决问题,一个单位缺了谁都照样运转,但我不想因为私事给别人增加负担,一个萝卜一个坑,我逃避了,必然有另一个人加倍承担。”闻者皆动容。
后 记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我饱含泪水写下几行字,却怎么也挽回不了您一去不回的事实,怎么也回不到十年前初见时的坦荡与不羁,那个时候不用想着哪天会离别,只管提溜着个地质包跟着您、听您安排,从早到晚、从南到北……
“长空俯仰无牵挂,心在高天暂突围。”“老学徒”奔波大半辈子,走遍了福建的山山水水,是该回归家庭享受天伦之乐了。但是,新学徒恳求您常回泉城走走看看,可好?这里有您奋斗过的痕迹,有您共事过的战友,有我们十年的师徒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