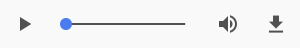
野草不知名姓,不知来历,就在巷陌田野,在贫瘠的夹缝间顽强地生存着,就像大自然给人类的一面印鉴,映照着过去与未来,映照着我们自身与身边的人。它们的世界让人费解,总以寂寞的方式在世间永恒存在着,一点点土壤就可以让它们绽放碧绿。泥土在,它的生命就在。它经受着人们的鄙视与蹂躏,甚至是锋利的农具给它们带来的灭顶之灾。它隐忍,它慈悲,它先于我们抵达泥土,为动物准备好赖以生存的食粮,还有治疗的草药。我们的身体也常被它包围,或者说它的绿色本就融进了我们的骨血之中。当我们远离泥土,远离乡村,在钢筋水泥的森林里迷失了方向,对它们只有伤害、背叛和冷漠,但它们还在守望着,像一盏灯,照亮我们的孤独旅程。
“年”在许多人的记忆里是充满欢乐的,从腊月开始,如同春潮般,游子不断地回到故乡,只为回家过年,就像村头那棵大树,树枝很多,但根只有一个。
北方的冬季寒冷干燥,记忆里围坐在“红泥小火炉”周围,茶炉里咕嘟咕嘟的水声如同每个人脸上的笑容一样乐开了花。最喜欢外面黑云压城般下着大如席的雪花,这时人们聚在屋子里围着火炉有说有笑,其间偶尔出去踩几脚雪花,也散散身上的热气,就这样一直到深夜,然后一觉醒来,白茫茫的大地真美啊,在院子里堆雪人,找个坡路滑雪,眯着眼眺望银装素裹的大地,以寻找天地交汇处……想想都觉得满是童年的趣味。真想每年回家都会有这样的大雪光临我的故乡,那该多么幸运。可是现在每年都是干冬,雪几乎成了奢求,更别说如那记忆里的大雪了。
村子里每年会选两家当“会长”,我家是今年当选的其中之一,有位老人说我们村的人一生最多也就只能当两次会长,所以每家都很用心。山神庙旁边有一个古老的柏树,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有多大年龄,平常日子还好,只是在过年它就变成了顽皮人的炮架子。今年过年时,见树上挂了块牌子,提示保护古树,村民不想让这个故乡的“标志”那么早枯死。
村里的头号大事就是正月初八的社火表演,正因为如此,我们村一过初八,年就算过完了,外出为生计打拼的人如同候鸟一样,随着几声鸡鸣他们准时离开了家。外出闯荡有了结果的人在城里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有了不错的工作,高额的工资把一个家渐渐地撑起来,这是我们泥土里长大的孩子最高的“丰碑”。
故乡里的人,有的过得欢乐,有的过得忧愁,有笑声处就有哭声。最伤心的莫过于一位父亲撇下还在读小学的儿子就撒手人寰,使原本生活拮据的家更是“雪上加霜”,路遇那小小的身躯披一袭孝衫,被此情此景绊住了脚步,顿感人生苍凉。生存与年龄无关,真心希望这个孩子也能自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又一个年就这样过了,一路上既有收获,一年到头也就这个时候能陪家人十来天,能逗奶奶多笑一笑;也有遗憾,过年打算拍个全家福却没有拍成,家长虽然没说,但也做了些团圆的准备,却落了空,只能等到来年再拍了。
每次回家,留在故乡或记忆里的只有衰败的土坯屋,还有村旁一座座逐年增多的坟墓。那逝去的亲人,唯有梦里相见;远在他乡未归的亲人,或许一生也难以相见。回味从前,那些朴素的音符昼夜敲打在我们日益老去的身骨上,在灯红酒绿、醉生梦死后,还有一丝苦涩和温情,让我沿着弯弯的阡陌回到老家,朴素生长,看云看天看地,让叶抽芽、枝开花,然后在秋风秋雨中枯黄老去。年是以苦涩之后的温情告一段落的,像长途跋涉之后终于到达目的地,有阳光有清泉,我们都知道这不是故事的终点,伤痛也是抹不掉的。在老人看来我们这一代是幸运的,如同《崖边报告》中描写的一样,在城市化大进程中某些乡村或许会消失,这故事本身就让人哀伤,期望我的故乡不在他的预言之中,最起码在垂暮之年的某一天,我还能踏在故土上,怀念以前的光阴。故乡在,光阴就在。
故乡的每一种植物都是一盏灯,照亮了每一个游子回家的路,野草啊,他们像大地的耳朵,聆听着人世的悲欢离合,它们也像大地的书写者,以一种我们不认识的文字记录着年复一年的生生死死、荣枯与离合。就像一首歌里唱得那样:
没有花香,没有树高
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
从不寂寞,从不烦恼
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