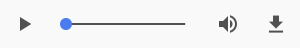
一
正午,山上。
翻过山脊,视线一下开阔起来,坡上是层层叠叠的梯田,如花边一般层层铺开。风正路过,调皮地踮着足尖在玉米叶上一路小跑,掀起细碎的波浪,窸窸窣窣,如田间的窃窃私语。阳光落下来,密而明亮,空气中氤氲的热气网一般罩着他。
他脱下工衣,绕着点位左右看了看,地形开阔,平整。他放下东西,开始架设仪器。
等待数据采集的时间是悠长而乏味的,全站仪像一个忠诚的士兵,挺拔地伫立在烈日下。他却听到了肚子“咕噜噜”的抗议声,这才想起来,从早晨到现在只用一片面包果腹,这会儿能量早已消失殆尽了。
于是就近寻一棵树,顺着树干出溜下去,一屁股坐在地上,巨大的树荫拥他入怀。
他打开随身的背包,拿出午饭:面包、火腿、矿泉水,顾不得擦手便大口吃了起来。
背包是父亲发的,很耐用,厚实的帆布挺括而结实,他每次出野外都会背上。
父亲与他同在一个单位,工作性质亦无差别。
在他印象里,父亲很少在家,长年累月不见人,帆布包、大头鞋是他最亲密的朋友。
父亲也不像班上其他同学的家长那样,出远门回来总会带一两件玩具,父亲只会带些土特产,核桃或者柿子,以至于到后来他对这两样东西看都不想看,更不嘴馋。只有一次,父亲从北戴河回来给他带了两个海螺,一个有拳头那么大,用嘴使劲吹还会发出呜呜的声音。他把海螺凑到鼻子尖,一种淡淡的盐腥味扑面而来,像梦境中大海的气息。从此他开始向往大海,向往有浪花拍岸、有柔软沙滩、有优美地平线的广阔世界。
父亲在参加工作的第二十个年头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那天他像往常一样放学回家,一步两阶地跨着冲上五楼,推开家门那一瞬间却愣住了。屋里有很多人,三三两两地坐着或站着,母亲在沙发上低着头,似乎在哭。
看到他进屋,所有人都沉默着把目光转到了他身上,又极快地移走了。
叔叔悄悄把他拉进屋,告诉他,父亲没了,泥石流,为了保护仪器。他不敢相信!那一刻,他满心满眼都是父亲那张熟悉的脸,棱角分明而略显沧桑,慢慢地,那张脸在母亲的哭泣和旁人的劝慰声中消散、隐没。伸出手去,他再也没能触到父亲的体温。
“嘀,嘀,嘀”,时间到了,仪器发出蜂鸣声,他站起身去收仪器,在心里默想着下一个站点的方位。
他拎着仪器、挎着背包向山坡下走去。
父亲出事后,单位负担起了他和母亲的生活,并且供他读完大学。他学了父亲的专业:测绘工程,并回到了父亲的单位工作。大海已经离他越来越远,踏着父亲的足迹,他爱上了这连绵起伏的大山。
二
夜色弥漫,井口的灯光虽然热烈而奔放,却没有激起矿山喧嚣的欲望,大部分声音和身影都隐没在夜色中,只有头顶几颗星星目不转晴地注视着这几个忙碌的测绘人。
选择在夜里施工,是为了不耽误矿上的生产。主任说,测绘技术服务,说到底还是服务,除了必须的严谨认真外,还要有服务意识。
如果在两年前,他大概不会同意这种观点。他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目标是搞科研。所以在考进这个事业单位之后,一次又一次的野外施工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心理落差。他没有办法接受在完成四年高等教育,走出象牙塔之后,却要每天穿着粗糙的工作服,拎着笨重的三角架爬山;也没有办法忍受早出晚归,常常天不亮就走,月亮高挂还没返回的情形;更没有办法面对回家后镜子里那张胡子拉碴、皮肤黝黑的面孔。那曾经是多么英气的一张脸啊,现在,简直就是一个有大学文凭的农民工。更难以接受的是,因为工作繁忙,单身的他想去相亲,却连个合适的时间都挤不出来。一想到这里,他就懊悔不迭,怪自己当初脑子进了水,选了这么个行业。
搭档的师傅看出了他的小心思。
师傅姓李,外形犹如刘文西笔下的老农,阡陌纵横的脸上烟火沧桑,稀疏的灰发倔强地匍匐在额头上,维护着零落前最后的尊严。
李师傅是个老测量,18岁参加工作,从驻扎工区,居无定所,到回归大楼,授技带徒。40年里,他练就了一身本领,各种仪器一学就会,识图看图更是火眼金睛。在野外施工,尤其是工程测量中,他就是徒弟们的定心丸,跟着他,徒弟们飞速成长。
有一次干完活儿,大家坐在地上休息。他无意中看到李师傅手机里翻拍的一张照片,泛黄的颜色,像岁月的底色,剪成花边的方框里,几张意气风发的年轻面庞,笑容灿烂如初秋的阳光。“这是谁?是你吗,师傅?”他指着其中一个似曾相识的面孔问。李师傅没回答,却有几分得意地笑了。“哇,你年轻时候这么帅!”他不由脱口赞叹。“那当然,谁说老太太当年不是大姑娘,你师傅我年轻时候也是鸿图大志,英俊潇洒呢。”说完,李师傅哈哈地笑了。然后话锋一转,说道:“可活儿得一点一点干,饭得一口一口吃不是?谁的本事也不是想出来的,是干出来的呀!”说完,师傅拍拍他的肩,微笑着起身走了。他却心绪纷乱起来,师傅最后那句话像拨片一样触动了他。那天晚上电视新闻专题播放了我国北斗系统建成,他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渐渐地,他与自己达成了和解,不再好高骛远,在琐碎的日常施工中投入了全部精力。
五点,井下和地面的工作全部完成。天色开始由青转白,有薄薄的雾升上来,在天地间荡漾成一缕细纱。
他伸伸腰,作了最后的检查,心里对自己又完成一次肯定,然后手一挥,潇洒地对同伴说:收工!
三
傍晚,远郊。
曲曲弯弯的小河从桥那头流过来,又顺着小路哗啦啦地流开去,溅起的水花泛着白色的泡沫。
他沿着河边走边看。河水浑浊,和他的想像截然不同,黑绿色的河面上有时还会漂浮着一些性质不明的污物,散发出隐约可闻的腐味。
他一边走一边拍照,有时会停下来支好仪器测个位置。这个项目由他独立完成,所以他格外谨慎。
今天他已经走了十几公里,从图上看,这条河还有四分之一就到头了。这会儿他微微带喘,额头也渗出了汗珠。
他稍作休息,顺便掏出手机。“叮咚”一声,传来一条信息。
他点开微信,是老婆发的:妈来了,我也和同学联系好了,明天带她去医院。
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母亲耳鸣有一个月了,给他打电话说想去医院,他却总是抽不出时间。
对家里,他是有许多愧疚的。
“叮咚”,又是微信的声音,他点开,还是老婆发的,是一条小视频。视频中两个装扮搞笑的演员在演双簧。坐在凳子上的男扮女装,鼻梁上擦了白白的粉,头上顶着一个冲天辫,表情夸张地念白;蹲在身后的捏着嗓子阴阳怪气地说:“好女不嫁测绘郎,害得老娘守空房。”配合着话音,前面的演员一拍大腿,一边伸手探身,做势要去追人:“喂喂喂,你去哪儿,你给我回来……”台下观众一阵哄笑。
他也忍不住笑了,嘟囔了一句:“这是敲打我呢。”
他给老婆回了个抱拳的表情,又发了一朵鲜花。
像是卸下了一副担子,他又满血复活了。
拿起仪器,他又开始沿河而行。身后,晚霞正一点点落在他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