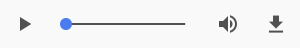
诗经有云:“谁谓河广,一苇杭之。”韦一杭说,她的名字就来源于此。禅宗里达摩祖师也曾有“一苇渡江”的故事。河虽广,折一苇入江,化一叶扁舟,飘然以航,说不出的洒脱和快意。
在大学里,韦一杭学的是路桥工程专业,我学的是测绘工程专业。我们相识在一次选修课上,当时我被她课堂笔记上俊秀的字体所吸引——她的笔法是“赵体”。出于对书法的共同爱好,我们成了至交好友。
习字的人都知道,临帖最磨人心性,一纸赵孟頫《洛神赋》书法帖902字,一杭能安安稳稳坐上一天全部临完。羸而不弱,纯粹自律。
毕业后的一杭真的去造桥修路了,而且还修到了国外。入职央企的一杭乘着“一带一路”的东风,飞到了非洲,从埃塞俄比亚到坦桑尼亚,这一干就是四年。2013年3月份的某天,我收到一杭发来的一段视频,连绵的雨中,坦桑尼亚的一处乡间公路正在施工,头戴草帽、身穿工服的一杭正带着工人,对公路作业面的边边角角进行快速修补,身旁的作业大车轰鸣着往下撒布石屑。有人喊了声“一杭”,转过来的是一张清澈飒爽的笑脸。
非洲,乡间,大雨,修路,女孩。前四个原本就不算温和的词此刻组合在了一起,以一种更巨大的“杀伤力”冲击着最后一个词——“女孩”。女孩没有“醉卧杀场”的悲壮,亦没有“勉强终劳苦”的不快,而是以爽朗的笑容,将这五个词串联在了一起,勾勒出一幅“在友邦劳作忙”的画卷。原来真正温煦的美色,都熨帖着最质朴的真实,蕴藏在最平凡的人儿身上。
谁谓河广,一苇杭之。从中国到非洲,又何止隔着“河广”,可是一杭就是这么渡过来了。以至于几年之后再见到一杭,我发现她原本白皙的脸上竟然入乡随俗般染了非洲的黑红,手背上也已干裂脱皮。
如今的一杭,还是在到处修路。毕业十年了,从技术员到项目负责人再到技术总工,无论身处何种岗位,一杭最喜欢坚守施工一线,永远“灰头土脸”。
有人喜欢探险,喜欢在刺激中追求绚烂的生命伸张。有人喜欢安静,一粟一蔬一羹汤,细细品咂时光流淌的味道。有人喜欢奔波,痴迷于踏上不同颜色的土地,让陌生的气息浸透四肢百骸。他们目标不一,却都在自己的朝圣之路上,无比虔诚地向前走。
所以,一杭选择他乡,选择烈日,选择冬雪,选择尘烟漫天、挥汗如雨的施工一线。我明白,她喜欢这样,喜欢项目从图纸到竣工每一步的丝丝入扣,喜欢一次次坚韧果敢地解决好每个施工难题,更喜欢走在修好的公路上,看奔驰的汽车从身边呼啸而过,让那种心底泛起的成就感溢于言表。人可以志山,可以志水,可以志仕,为什么不能志在修路呢?生活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注脚,“雨中吃土”的纯粹,看似荒诞,却是一杭最爱的节奏。
看一杭奋战的背影,看她笑靥如花,看她对挚爱工作的沉醉,我发现,原来生活可以有这么多维度去诠释,不用踮起脚尖努力张望,只需遵循内心的呼唤。
致敬每一个人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