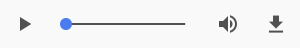
母亲在家中种了一池荷。
广而深为“湖”,湖连湖为“泊”。母亲种的荷花既不在院旁的湖泊里,也不似别人家种在青石雕琢或陶铸的缸中。荷花种在二楼平台的角落,是沿墙体砌筑成的一个高三十厘米、面积约四平方米的小池。池子从建成后便一直荒废着,母亲说想种些荷花,父亲说找不到合适的藕。母亲又说要不养些金鱼?父亲说再等等吧。这一等,便是数年。
有一年冬天,父亲从老家背回来三段藕,是从大伯家的池子中挖出来的。老家距我家约三个小时的车程,父亲从袋子中取出藕节时,附着在藕身上的淤泥还有些冻手。全家耗费一个下午的时间将小池清干净,母亲找来三个旧花盆,取来土,将藕埋在花盆里,再把花盆放入池中,然后把池中蓄满水。父亲用装修房子时剩下的瓷砖盖住小池,生怕冬天水面结了冰。
三个月后,一枝荷梗探出水面,再往后第二枝、第三枝、第四枝……六月初,巴掌大的荷花露出了粉嫩的笑容。待到三两朵高低错落,与碧绿荷叶错落地排列在那小小的四个平方里,透过夕阳映照在池子后面的白墙上,俨然一幅和谐有章的国画,直压得池旁那一排盆栽月季失了颜色。
一直以为荷花只开在盛夏,没想到六月里,小池中荷梗便接二连三地冒了出来,荷花一直开到了九、十月,开到了我的儿子满月。母亲抱着孙子,站在小池旁,又是一抹斜阳,白墙上的人影在点点荷叶间闪烁,一幅画有了人的参与,更显生机。那一刻,孩子粉扑扑的小脸像花儿一样绽放。
又是一年,小池又有了新的意义。我的母亲扶着孙子站在小池边,孩子刚刚站稳,一只手伸向池里,小小的手掌如莲蓬一般,试图投入荷花的怀抱。母亲随口念出杨万里的《小池》“小荷才露尖尖角”,也不知母亲口中的诗,说的是花,还是孩子。孩子咿咿呀呀地,像是重复着母亲念的诗。从此,这一池荷更有了诗意。我从别处买了十几条红金鱼投入池中,母亲念的诗中便有了“鱼戏莲叶间”。父亲又在池边安置了一个四十厘米高的假山,从此母亲念的诗中便有了“百里青山十里溪,荷花万顷照红衣”。
经过一家人的精心培育,小小一池荷从四五枝、七八朵,到一整面墙的粉红碧绿,四个平方的池水中游满了金鱼。孩子越长越大,母亲的诗教得越来越多。直到有一天,孩子成了哥哥,牵着妹妹的手,妹妹刚刚站稳,一只手伸向池里,哥哥又将《小池》念给妹妹听,妹妹咿咿呀呀地。哥哥调皮,折下一只嫩莲蓬放在妹妹的掌心。我赶紧抓拍下这张照片,将两个稚童定格在画面中。这幅画,就叫它《莲子》吧。
后来,全家老小也曾游玩各大名湖,北京的昆明湖、南京的玄武湖、杭州的西湖,无一例外,接天莲叶,映日荷花。广而深的湖面上,硕大的荷花铺满了我们的视线。若说这些湖中的荷与母亲家小池里的荷有什么区别,可能是花朵大了些,观荷的人多了些。斜阳夕照,清风荡漾,不一样的景化成不一样的诗句,却有着同样的诗意。无论是万亩还是四个平方,荷花都开得红红火火。小池的景致就像是缩小版的山水长卷,不信你看画中,广而深的湖,湖畔念诗的游人,还有赏荷的孩子们,孩子们的笑脸,都如荷花般粉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