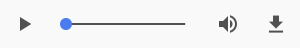
打开厨房吊柜门,里面整整齐齐摞了不下二十只盆盆碗碗,这些都是我参加工作后,母亲为我打下的“江山”,有粗瓷海碗、搪瓷碗、细瓷大小碗和不锈钢饭盒。
别看它们如今像是被打入“冷宫”,当年却是风光无限,好不威风。这一只只空碗曾经一次次盛满美味的肉臊子,那是以前每次我从老家返程时必带的沉甸甸的礼物之一。
在我返程的前一天,母亲都会准备好肉臊子。有时我没有提前和家人说返程时间,母亲则会带着一丝埋怨,匆忙拉着父亲去菜市场购买最新鲜的猪肉,回来后又马不停蹄地开始准备熬制肉臊子的一系列繁冗费时的工作,比如拔猪毛、洗肉、绑扎调料包等,然后用那把厚重的铁质大菜刀切肉、剁肉,最后炼油、烧水、炖肉……
大铁锅的锅盖不算轻,虽然可以勉强压住锅里咕嘟咕嘟沸腾的肉汤,却丝毫没有办法阻挡那一缕缕醇香缓缓飘出,不消半日,整个院子就弥漫着阵阵肉香。当然,等到肉臊子彻底炖好,还得些火候呢。终于,灶膛的火苗跳完最后一支舞,筋疲力尽地谢了幕。此时,锅盖也如释重负般被搁置一旁。
小时候,母亲做肉臊子时,总是让我和弟弟先尝一口,看熟了没。我们尝过之后,每次只会回答两个字“熟了”,除此之外再无多余的言语。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的母亲一定是失落的吧。其实她早就知道答案,无非是想让我们早一点尝到她亲手做的美味罢了,如果能得到几句赞美,便是对自己辛苦付出最好的鼓励和回报。可惜以前的我们根本不懂,现在更是不好意思说出口。好在我的孩子无师自通,经常夸赞母亲做的饭菜好吃,这也算是对母亲迟到几十年的宽慰吧。
以前,每次起锅后,我和弟弟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啃排骨。不过,在啃排骨之前还有一道小零食,那就是炼猪油时产生的小而脆的淡黄色“锅巴”,最后才是用热腾腾的白馍馍夹上香喷喷的肉臊子的肉夹馍。
母亲平时盛放肉臊子的容器是一个厚实且内外发亮的广口大肚枣红色瓷盆,外形有点像缩小版的水缸和面瓮的结合体,这是外婆留下来的。听姨姨们说,外婆做肉臊子的手艺是顶好的,以前过年时,把做好的肉臊子保存在瓷盆里,一直到夏天收麦子时都好好的。
肉臊子放凉后,上面会形成一层白蜡似的凝固猪油,戳上一筷子,除了能看到红红白白的肉臊子,偶尔还会在容器边缘发现少许薄如蝉翼的黄色半透明冻肉。如果有刚出锅的热馍,趁着热气夹进去几筷子,似乎还能听到一阵微弱的冻肉消融之声,伴着一股香气从热馍掰开的缝隙中四溢而出,咬一口下去,唇齿留香,回味无穷。直接拌面也是可以的,或者在馏馍馍的时候顺带热一碗肉臊子,又是别样的风味。
肉臊子不仅可以夹着吃、拌着吃,还可以在素菜快炒熟时丢进去几团或几片,迅速用铲子翻炒均匀,伴着一阵清脆的锅铲协奏曲,一道美味佳肴便诞生了。
无论哪种吃法,都是那么朴实,即便是见底的“油根儿”,用一小块热馍蘸一下,也能让我无限回味,每一口不仅是浓浓的乡情,更是母亲殷殷的爱。
如今母亲上了年纪,肉臊子做得比以前少了,橱柜里这些曾立下过“汗马功劳”的盆盆罐罐就“赋闲”下来。尽管它们做过“肥差”,却从来不做“揩油”或“中饱私囊”的事情。它们更像是肩负使命的使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传递着母亲对孩子的关爱与呵护。
我想,母亲喜欢做肉臊子不只是因为厨艺精湛或者热衷于此,在她看来,这是最好的营养滋补品,最宝贵的东西自然是要留给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母亲的世界很大,大到可以包容世间万物;母亲的世界又很小,小到心里只装得下自己的孩子。
长大后我才明白,那一碗碗看似平常的肉臊子,倾注了母亲对儿女全部的爱。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能吃到一口母亲或者姨姨们做的肉臊子,我就仿佛置身于故乡,回到了母亲身旁,因为这口肉臊子里不仅有美味、有亲情,还有家族的传承和我对故乡的深深眷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