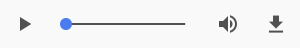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苏味道的这首词,生动描绘出唐时元宵佳节的欢乐场面。在这盛大的节日面前,对于童年的我而言,快乐盈满心间。
正月十五这天,早早起来的我就盼着天黑,怀里像揣了兔儿似的,蹦来蹿去,一刻也闲不下来。天微黑,母亲就把年前早已擦得锃亮的煤油灯一一点燃,素来节俭的她这时大方得很,灯捻儿挑得老高,灯光倍儿亮,堂屋、东屋、西屋、厨屋都被照得亮亮堂堂,连鸡窝和猪圈跟前也都点上了平时攒下的蜡烛头。母亲把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期冀都寄托在这小小的灯盏上了。她笃信,元宵灯亮,家旺年丰。
而我那颗痒痒的心早已飞向了街头巷尾,急不可耐地点上父亲给我做的花灯。灯是用竹篾绑的框架,裱糊着写对联剩的红纸,从点心盒上剪下的彩画作点缀,甭提有多好看了,绑到麻秆上开心地提着,出门走东串西显摆去。大街上灯火点点、热闹非凡,纸糊的公鸡灯、罐头瓶改造的玻璃灯、玲珑的橘子灯、笨拙的南瓜灯、漂亮的山羊灯、健壮的公牛灯,造型各异,令人目不暇接。村庄的戏台前,有人三五扎堆评说着谁的花灯漂亮,得到赞许的人便会暗自得意。我们一行十几个孩子,疯跑、嬉闹、推搡,只听“啪”的一声,有小伙伴的灯碰坏了,瘪嘴便哭。我们齐唱“灯笼会、灯笼会,灯笼灭了回家睡”,他瞬间破涕为笑,跟着一块儿哼唱歌谣。
那时候乡下很穷,看烟花、看社火只能到几里开外的集上。家乡所在的集市是公社所在地,街上张灯结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热闹的气氛。五颜六色的烟花,光灿灿、亮艳艳,那般漂亮、绚烂,有的如天女散花,有的似铁树开花,把整个乡村点缀得风情万种、美轮美奂。就在烟花绽放的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在元宵夜会有放烟花的民间习俗,为什么每一年人们争相去看烟花,那是大家对新的一年的美好希望啊!公社组织文艺宣传队敲锣打鼓、扭着秧歌、驮着背阁、舞着狮子,一路欢歌向街心走来。街道两边纸糊的灯笼高高挂起,整个大街通明闪亮,展示着民间风情和民间艺人的风采。街东头的舞龙队和街西头的高跷队像潮水般汇集而来,时而上下舞动,时而快速行走,时而翻腾打旋,仿佛一条巨龙在盘旋、欢呼、雀跃,村庄以民族的图腾将年推向了高潮。大街上摆满了地摊,卖什么的都有,滚元宵的摊位也一家挨着一家。路两边的树枝上挂满了星星般的彩灯,满街乌泱泱的人,孩子们就像一条条小鱼穿梭在人的海洋里。传统的节日文化为这个萧瑟的季节渲染出绚烂的诗意。
集市南街是观灯区,川流不息的人群与灯火的海洋交织在一起,营造出浓浓的文化氛围。父亲背着妹妹,我紧拽着母亲的衣襟,满街花灯,花团锦簇,灯光摇曳。大红灯笼自不必说,招人稀罕的是八仙过海灯、猪八戒背媳妇灯、兔子灯、花卉灯、鸟禽灯等。五颜六色的灯笼上写着祝福语、诗词,更多的则是贴了写着谜语的纸条,供游人猜。我一看,高兴得一蹦三尺高,猜灯谜对我来说可是小菜一碟。“远看像牛,近看没头(打一字)。”我眉头紧皱,眼睛盯着谜面,苦苦思索着,终于想到了“午”这个字,我赶紧把谜底贴到谜面下面。字谜答对了,我的眉头也松开了,心中无比喜悦。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色彩斑斓的焰火、铿锵有力的锣鼓、五光十色的花灯把深浓的夜色熏染得红彤彤、暖融融,把寒夜的料峭驱赶得一干二净,也在我的记忆时光中留下了美好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