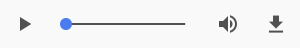
腊月里的雾气总在清晨爬上窗棂。奶奶蹲在灶膛前添柴,蒸笼里窜出的白气把她的银发染得湿润。当一屉屉白胖胖的馒头伴着香气出锅,年糕的甜香和排骨的肉香渗入每一根房梁时,我就知道,这条叫作“年”的河流开始涨水了。
裁缝铺的布匹在玻璃柜里泛着绸缎般的光泽。母亲总要对着月历数上三遍,才舍得剪下那块暗红格子呢。缝纫机的嗒嗒声穿过冬夜,针脚里藏着新棉花的暖意。父亲在檐下杀年猪,刀锋在石磨上霍霍地磨,惊得麻雀振翅掠过结霜的柿子树。
除夕夜的鞭炮炸开旧年最后的褶皱。我们踩着红纸屑跑过大街小巷,家家户户的门缝里都淌出金黄的灯光。八仙桌上的铜火锅突突冒着泡,水汽漫过爷爷褪色的中山装,在玻璃窗上凝成细密的水珠。守岁时数着座钟的嘀嗒,困得眼皮打架也不敢睡,生怕错过岁末最后一粒星子坠入人间。
初一的晨光里,新棉鞋踩着结冰的田埂。蓝布衫口袋里鼓鼓的,装着压岁钱、炒瓜子和炒花生。大伯家的门环叩响时,屋檐下的冰凌正融出第一滴水。满屋子蒸腾的茶香中,姑婆们围坐炕头,把一年的光阴掰碎了放进芝麻糖里。
元宵节的灯笼游过村口老槐树,纸扎的鲤鱼灯笼在风里摇头摆尾。我们举着蜡烛满村跑,火光在瞳孔里跳成小小的太阳。直到最后一盏红灯笼隐入夜色,年河才渐渐退潮,留下满地彩纸,像散落的桃花瓣。
如今,超市的速冻年糕在微波炉里打转,视频拜年的笑脸嵌在荧屏的冷光里。但每当年关将至,母亲仍会固执地蒸起那笼红糖年糕。白气升腾的刹那,我总能看见时光的褶皱里,那个在灶火前等待的孩童,正踮脚数着蒸笼里层层叠叠的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