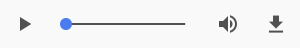
入了秋,一早一晚,天气明显凉了。
都秋天了,还有这么多的蚊子,年逾八旬的老母亲颤巍巍地点上蚊香,敬神一样,把这微暗的“烟火”送到老房子的角角落落。他跟在母亲身后,安心而自在。
他在地质队搞测量,刚毕业时,常年在野外忙碌,每年春节才有时间带着妻子和孩子一起回老家。如今,他调回机关工作,回老家的次数也多了起来。每次回家,他总是忙前忙后地护着母亲。母亲的腿脚不中用了,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像踩棉花包,陪伴母亲的日子,注定是不多了。
他是母亲四十岁时才结下的“秋葫芦”,小时候,父母把他看得比命还金贵。父亲病逝后,母亲在乡下独守,过着清冷寂寞的日子。每隔十天半个月,他就要回来看看,村里人都说他是大孝子。
其实,他的心一直很不安。“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可得见者,亲也。”他怕不久的一天,母亲会离他而去。
十只小鸡仔在母亲的“指挥”下钻进鸡笼里,鸭子也进圈了。母亲正准备插上吱呀作响的大木门,他笑着说:“娘,今晚的月姥娘多好呀,咱们到院子里看看月姥娘吧。”
在惠济河边的豫东老家,他们喊“月亮”为“月姥娘”,多温馨呀。他依稀记得小时候母亲教他的歌谣:月姥娘走,我也走,我给月姥娘提背篓。月姥娘来,我也来,我给月姥娘去劈柴……他心里念念不忘小时候有“月姥娘”陪伴的往事。
有一年,也是深秋,那天是周末,因为周边村子都停了电,打面机用不上,他和母亲只好拉上板车,去县城里磨面粉。队伍排成了长龙,等他家磨好面粉时,已经是夜里九点多了。
走到县城的东门口,母亲破天荒地“潇洒”了一回,给他买了七个生煎包子。母亲小心地用四方手绢包着,全递给了他。私下里,他认为只有那一次的生煎包子,才是他这半辈子吃到的最好吃的美味。
“月姥娘”一直跟着他们走,皎洁的月光如水般流泻下来,照着母亲清瘦的脸庞,也照着茫茫的四野。泥土散发的湿漉漉的气味,芳香着周身。他拉起板车来,劲头十足。
近了,村口的那棵老槐树,尽管树影黑成一大团,传来的婆娑声很是熟悉,还会听到几声狗叫,因为有母亲在,他是不会害怕的。那时候,母亲多年轻呀,走路像一阵风。
今夜,又是“秋蝉满枝响似筝”的时刻,他和母亲坐在院子的石板上,就着可以佐酒的月光,他又开始劝母亲和他一起进城生活了。他和妻子省吃俭用,特意买了一套四室两厅的房子,足够大,一家四口住得下。母亲苦笑着说:“我都成了一把老骨头了,前辈人常说,‘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九十不留坐’,还是在家好。我的‘大褂子’都油漆好了,哪一天闭上眼,也不怕。我一甩手进城享清福了,留下你爹,咋办?他可是苦了一辈子呀。”那一刻,他终于明白了,故乡,是属于老年人的。这个月光下的小院子,永远是他难以割舍的心灵脐带,是他最放心又最不放心的地方。
落下了几片石榴叶,声音尽管很轻,但他分明听到了。他向母亲聊起当年在地窑子里烧红薯的事,母亲一下子来了精神。那也是一个秋夜,干柴燃尽时,母亲从火堆里给他烧红薯,不停地替换着双手剥红薯皮。看着他吃得满嘴灰黑,母亲笑了,他也乐了。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日子过得多快呀。
他抬起头,家乡的那轮明月在寒空中高悬,仿佛在和他相认。夜,一寸一寸地深,清月照着瘦影,他伏在母亲的肩头,聊着开心的往事。忽然,母亲话题一转,郁郁地说:“孩,记着呀,给你们买的二十斤土花生,放在东屋的面缸里。你给的钱,我花不完,全放在你爹的大瓷相后面……”他心里隐隐一疼,眼泪唰地流了一地。







